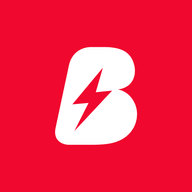“逍遥”是联绵词,以其叠韵的回响联绵出天籁浑然的节奏。大道浑沦,无以名状,唯借此音节之谐振而留响于人类唇齿,发而为言,幻而为人为事为草木虫鱼鸟兽之声,如钟声之余韵,协和万物之舞蹈,纷然杂陈于斯,乃命之庄子,乃谓之逍遥。
然而,《逍遥游》开篇却已是判然两分的南海北海,以及南北海之间的巨大时空。如何通过鲲鹏的转化和大鹏的飞翔来重新贯通南北,融合天池之明与冥海之暗,飞回原初的浑沌一体,正是《逍遥游》的任务,同时也可能是全部《庄子》的基本任务。
内七篇最后的浑沌之死也许是《逍遥游》开篇鲲鹏故事的前传,而逍遥要解决的问题正来自浑沌之死。逍遥是浑沌凿破之后,对浑沌的工夫论重生,正如“道行之而成” 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 是对“道可道、非常道” (《老子》首章) 的行动生成。
浑沌之所以会死,其实在“中央之帝为浑沌”的名词化命名中已经暗示,不必等待儵、忽的凿破。相比之下,逍遥却一直保持为摹状的虚语,持久地抗拒着名词化的使用,即使只是寓言式的命名也不见于《庄子》始终。


汤之问棘也是已:穷发之北,b体育有冥海者,天池也。有鱼焉,其广数千里,未有知其修者,其名为鲲。有鸟焉,其名为鹏,背若泰山,翼若垂天之云,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,绝云气,负青天,然后图南,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:“彼且奚适也?我腾跃而上,不过数仞而下,翱翔蓬蒿之间,此亦飞之至也,而彼且奚适也?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这是鲲鹏寓言的第三重讲述。第一重讲述直陈其事,第二重讲述依托《齐谐》志怪,第三重讲述转述“汤之问棘”。第一重自语,第二重他言,第三重对话。有问有答,方为对话。“穷发之北,有冥海者,天池也……”这段讲述便是棘之答汤的记录。
在这重讲述中,北冥已然是天池,所以,这次的图南之旅不再是飞往天池,而是从天池的返回。所以,从飞往天池的第一重讲述,到飞离天池的第三重讲述,也形成了一个对话式的往复结构。考虑到《庄子》寓言多以对话出之,这里的对话式结构就尤值深思了。鲲鹏寓言的三重讲述都没有明显的对话形式,但在第三重讲述中却透露出这是一场问答的记录,而且深藏其对话性质于讲述方式的隐微结构之中,可能有着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。
第三重讲述中的小鸟斥鴳,亦不同于上次的蜩与学鸠。疏云:“斥,小泽也;鴳,雀也”,可见斥鴳是水鸟,比山林中的蜩与学鸠更加降低了身位,更近于冥海的低位。老子云: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为百谷王”(《老子》第六十六章)。以小泽对应冥海,以“翱翔蓬蒿之间”对比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,仿佛提示着一种返回:从冥海到小泽的返回,从青天到蓬蒿的返回,从扶摇而上到翱翔之间的返回,从一往无前的图南到往复彷徨的返回。逍遥之为逍遥的最深义蕴,可能就在这种返回。
庄子寓言的卮言两行吊诡性质提醒我们,不可轻易选边站队,选择大鹏或小鸟的一方视角来看问题。庄子的寓言作为一种卮言表达,往往内藏一种回环往复的结构于其中。所以,庄子寓言中每每充满了不易觉察的反讽和“正言若反”,需要读者通过反向阅读和理解的反转,才能实现寓意的往复和返回。
联绵词“扶摇”与“翱翔”的对举,微妙而精确地暗示了大小之间的“正言若反”。“扶摇”直上云天,“翱翔”回旋往复于周遭,这显示了大鹏小鸟之间的第一个区别。在这一点上,大鹏以志向之高远胜过小鸟的局限。第二个区别在于:“扶摇”言风,只是风的扶摇,大鹏乘风乃得向上;而“翱翔”却是斥鴳自身的翱翔。
这意味着,大鹏反而较小鸟更为有待,而小鸟则更加自由。这是一个隐微的但又是决定性的反转,它决定性地暗示了斥鴳是大鹏的返回。从大鹏之大到蜩与学鸠之小作为大之对立的小,再到斥鴳之小作为大之返回的小,小大之辩的寓言讲述完成了一次彷徨往复的翱翔之旅,并因而从小大之辩进化为小大之变。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斥鴳达到了大鹏的逍遥,或者比大鹏更逍遥。无论大鹏还是斥鴳,都没有某种固定状态的定性断言。逍遥与否并不是大鹏之大或者小鸟之小就能决定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,逍遥就太容易了,只要一味做大或者一味变小就可以达到,岂不荒唐?
事实上,正如船山所见,大鹏之大和小鸟之小都是妨碍他们达到逍遥的因素,因为大者困于势,遥而不能逍(逍亦作消);小者困于情,逍而不能遥,皆不足以逍遥。所以,欲致逍遥,须“兼小大”而后可(船山《庄子通·逍遥游》)。这便是“小大之辩”的真实意义之所在。“小大之辩”并不是为了争一个是非高下而去论战,而是为了达到“兼小大”或“小大之变”而作的辩证对话。“小大之辩”不是“儒墨之是非”一类的物论不齐之争,而恰恰是《逍遥游》中寓含的“齐物论”。
“扶摇”和“翱翔”是《逍遥游》文本乃至全部《庄子》文本中出现的第一对联绵词。此后,在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章深林,出现第三个联绵词“鹪鹩”,而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”之意,正同斥鴳之“翱翔蓬蒿之间”,都是小而自得之状。接下来在“肩吾问于连叔”章的“旁礴万物以为一”中出现了第四个联绵词“旁礴”,而这显然是一个“大的”联绵词。从鹪鹩之小到旁礴之大,可视为第二对联绵词。
联绵词本来就是“连语之字”(王念孙),而联绵词在《逍遥游》中的出现竟也是成对出现的,虽然这些对子并不总是紧连在一起,而是如“一阴一阳”般交替出现。这种成对出现的特点,正与“小大之辩”的主题相呼应,更与开篇就出现的南北海之间相对而相通的关系相呼应,乃至与内七篇首尾相连的浑沌与逍遥之关系相呼应。
“一对”既是一,也是二;既是相反,也是相通。中国诗词何以形成对偶、对仗的形式?其根源亦在于此。“明月松间照”,但也照在山石流泉之上;“清泉石上流”,声亦洋溢松月之间。相对之物如水墨相破、相互渲染,而又水归水、墨归墨,这便是“对子”的妙处。故程子读《易》,思及万物莫不有对而中夜舞蹈,其乐何如哉!
“旁礴”之后,《逍遥游》中还有两对联绵词出现在末章。一对是“臃肿”和“跳梁”,分别对应大树的无用之大用和狸狌的机巧而适足以自毁;另一对便是最后点明全篇主旨的“彷徨”与“逍遥”。如果按照前面三对联绵词的出现规律,“彷徨”与“逍遥”的对举应该也是相反的,或者说是貌似相反而其实相通的,但当这一对出现的时候,却发生了改变。在“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”的表述中,“彷徨”和“逍遥”更多体现出一致性。
不过,在其表面的一致性中,仍然潜藏着区别,乃至对立。因为,在这句话里,“彷徨”与“逍遥”并不能互换位置。“其侧”“其下”的范围虽然都在大树的周遭,但“寝卧其下”的梦境却可以无远弗届,突破树下彷徨散步的范围,混一南北冥明、咫尺千里、瞬间万年。“野马也,尘埃也,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”是大鹏之视下,更是寝卧树下的逍遥者所想象的大鹏之视下。在逍遥者“乘物游心”的想象或梦境中,在借大鹏之眼俯瞰万象的野马尘埃之中,在万类群生的气息相吹之中,他同样看到自己寝卧其下的大树,和他在树下逍遥寝卧的梦境。
如此,从“扶摇”返回“翱翔”,从“逍遥”返回“彷徨”,从远方返回近处,但已是不再逼仄的近处,寝卧者于是在天地之间完成了一个仰观俯察、“而上”“而下”的大循环、大往复、大彷徨。此“彷徨”名曰“逍遥”,此“逍遥”终归“彷徨”。非“彷徨”之近,无以至“逍遥”之远;非“逍遥”之远,无以返“彷徨”之近。所以,当最后在“无何有之乡,广莫之野”的树下“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”的时候,最后一对联绵词才完全实现对立中的联绵,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对。
如此,则远近联绵,小大联绵,“扶摇”联绵“翱翔”,“鹪鹩”联绵“旁礴”,“臃肿”联绵“跳梁”,“彷徨”联绵“逍遥”,日常联绵高远,“道不远人”联绵“任重道远”,莫非太极之两仪相推、浑沌之分化化合也。两仪相推,游也;分化化合,游也。游,则逍遥自在其中矣。故逍遥并非某种固定状态,而是日游日化的工夫,朝向浑沌复性的工夫生成。